目录
腊肠咬起来很辛辣。
“雷蛇,吃的习惯吗?”
芙兰卡问。
餐馆里,人来人往。
各种声音传来。
六点钟(不是我负责的区域,我继续向前瞄准,开火,判断局势,传达讯息,瞄准,开火,再次判断,再次传达讯息)坐着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太小,应该是在等大人点完菜回来;三点钟那桌(听到呼喊,我把身体缩进盾后,判断局势,向右索敌,开火),有个中年人在打电话,一直夹杂着口癖,但声音听起来让人挺愉快的,他是在和自己的朋友联系,可能吧,音调高昂,几个发音说的极为迅速,就像是一种单纯的言语上的连接;九点钟方向(清空),没错,被清空了,位置还空着,等待着食客;然后,十二点钟(评估场况,完毕,可以继续推进。)……也就是我的面前……
芙兰卡不见了。
“芙兰卡!”我失声大喊出来。
周围陷入了一片寂静,我似乎能听见那些眼神汇聚于我而发出的声音,像是行军时划一的跺脚声。哗!
“优等生,”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五点钟?六点钟?还是七点钟方向?在哪?)传来,“这样班长职位要被撤了呀。”
环境复归喧闹,不是芙兰卡说完这句话后,而是极为短暂的寂静,在芙兰卡的声音出现之前,她还未喊出我的昵称时,大家就又回到了各自在餐馆的生活节奏里,叮叮当当,碗筷声,大概。
我转头看向身后,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芙兰卡微笑地看着我,即使思绪刚刚如此繁杂,我却觉得自己只是一片空白。
芙兰卡身下是刚刚那位十岁左右的孩子,现在一位中年女性已经回到了孩子的身旁,芙兰卡对他们之中的某个人说了些什么,然后轻巧的向我们的桌位走来,我下意识的回头,刚准备坐下,发现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了,急躁地再次转过视线,她在我身后伸手轻轻地抚上了我的肩膀。
“要是一屁股做空了,可不好看啊,毕竟已经过了上学的年纪了。哈哈,不过这岂不是暴露了我小时候经常这么抽别人椅子吗。”
她把刚刚因为我突然起身而被推后的木椅向我这边推回来,椅座的边缘触碰到了后腿,我突然感到一种极度的安心感,顺从地依着芙兰卡的动作弯腰坐了下来。
芙兰卡保持着她轻巧的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蹦回了我的对面。
“刚刚是怎么啦?那么激动。”
“没,看到你不在了……”
“嗯?嗯——”
她开心的哼哼着,我几乎能够感觉到因为我刚刚慌张的回复,她面对那么多种可以捉弄我的回答,感到了一种幸福的烦恼。
“那,那个,刚刚你怎么会到那边去。”我赶紧岔开话题。
“啊,那个啊,”她眨眨眼睛,“刚刚那边的小朋友,可能是一个人有点害怕想离开座位,我看见他妈妈快要点完菜回来了,就走过去告诉了他一声。咳,”
“咳,咳。”
之后,她把手握成拳状抵在嘴前,传来两声粗重的咳嗽。
“芙兰卡……”我下意识的呼喊她的名字,但喉咙就像是已经声嘶力竭过了一般,这三个字几乎轻盈的像是个人的呢喃。
我再次站起身,试图接近她,但芙兰卡低着头,没有捂住嘴的另一只手向着我这边摆了摆,我只好在她侧边坐下。微微下垂的脑袋上,芙兰卡她毛绒绒的耳朵仍精神地耸立着,不同于坐在她对面,此时侧身看去,黑色尖尖的耳朵与液体般柔软绵密的头发衔成了光滑的曲线,追随流淌至长及肩部的发梢,我伸出手,却不知道想触碰什么地方,只能呆滞地停留在我与她之间的空气里,芙兰卡她没有继续咳下去,却依旧保持着刚刚咳嗽的姿势,我难以忍受内心的感情,握住了她的手腕,这时她才像是从睡梦中清醒了一般,向我这边抬起头来。望过来的黄色瞳孔,就像打落的生鸡蛋般,以一种脆弱的凝聚感滞留在眸的中心,四周颓去透明而均匀的水渍。
我强忍着因为突如其来的担忧而想要哭泣的感觉。芙兰卡把头快速的转向另一边,用指节擦了擦眼睛。芙兰卡她擦去的是因为病痛的眼泪……我由此感到自己感情的悲伤与她生理上的痛苦产生了低相性而带来的摩擦,我在这种摩擦的温度之中,感到剧烈的失重感。
新田火车站,新田,这么叫或许就是“崭新的田地”之类的含义吧,总之是一种傻乐般的俗套。
芙兰卡坐在车站的座椅上,看着发给雷蛇的地址——雷蛇保持着一脸放不开的严肃,低着头看着手机,然后抬起头一板一眼地询问路人。如果自己没有来接她,大概是这样的场景吧。
想象着她一丝不苟的动作和按部就班的问句,自己也不由得微笑起来。
一如既往,还想起了与大家离别前的雷蛇的声音。
已经来到这里疗养七个月有余,当初医生忽然通知到起码要待一年的时候,自己在医生那里闹了不小动静,拿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反驳医师过于理论化的用词时,芙兰卡却意外分神地联想起了战场上的自己:喜欢装作毫无防备的样子,特意把这种状态暴露给陷入优势或劣势的敌人,在他们自以为可以乘胜追击或是绝地反击时,突然挥击出迅速加热过后的铝热剑。在那些最为陷入苦战、装备最为厚重的敌人以此被击中要害时,敌人面容之中想要拼死压抑住的,除了死亡的恐惧,还有失手前一刻心理上的得意与笃定。
明明死亡将至,却还把这种错失的感情提及眼前来焦虑吗?
然而世界上笃定的事是难以信任的,能够充满自信的人也只有选择笃定一条路。
自己一般不会去思索这些,然而在基地最后一次面对医师时,却莫名思考起了这种相互吞噬的戏谑的逻辑感。
自己反驳医师时,突然内心就此被一种空虚袭来。
先前,即使医师只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与工作强度中某种缓慢的变数,芙兰卡也会对此作出各种狡黠的反驳,但已经开出的药芙兰卡依旧会认真服用,只是随着时间过去,自己偶尔会有那么几分钟,甚至是服药后不久,胸腔里的某处……疼痛得难以忍受。在几万个世纪过去的下一刻,自己抬起布满冷汗的头,却发现房间任何钟表上的时间都仅流逝了寥寥两三分钟。
自己顽固地将袭来的空虚无视,嘴上反驳医师的力度也未曾削弱,但却觉得言语刚脱出口腔,就在空气之中蒸发了。
这种空虚会将自己送去无休无止的休养,所以根本不用理会,反驳,继续反驳,它装作人畜无害甚至是为了自己好的样子,不就和主动露出破绽的自己一样,是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诡计吗!
……说到诡计。
这种战术倒是经常被雷蛇批评呢,说什么正常推进,一样能够在规定时间按照要求完成目标。
芙兰卡这种自我的战术确实在时间上对本组以及协同行动的其他小组提供过无数额外的珍贵机会,以及减少过在推进之中“正常情况下”可容许的那些伤亡”,将他们从死亡的数字里挽回为鲜活的生命。
这种空虚似乎进一步渗入了自己,不仅体现在对医师连绵不绝的反驳,连刚刚脑海里的这些想法也变得空洞了……
相互吞噬吗。
即使搭档了这么多年,雷蛇偶尔对自己性格上的判断有时候还是死板得令芙兰卡觉得麻烦,比如吃药的事情,雷蛇就一直喜欢提醒自己遵从医嘱,然而很多事情,包括服药在内,自己都是会去认真地对待的。
甚至可能不是觉得是觉得雷蛇麻烦,而是自己觉得生气么,是因为感到雷蛇没有对自己回应具体的关心,而是把自己的现状全部推给药品来解决了?其实不是的,自己或许只是想要雷蛇无时无刻的……也不能说关心,或许比较难懂,只是想要看到雷蛇无时无刻的那样呆板不苟的叮嘱,当然吃药也是叮嘱,但不一样,还是叮嘱这件事本身比较好。
自然的,和雷蛇搭档那么久了,难免还是会被她看到自己疼出冷汗的时候。
当自己咳嗽完,不知道是疼累了还是不想听她像往常一样再提醒自己吃药的重要性,闭上眼睛时,她却再没有从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听到一丝搭档的声响。
过了很久,那头才传来一丝模糊的吞咽声。
芙兰卡睁开眼睛,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雷蛇没有看向自己,只是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地板发愣,雷蛇的手悬停在自己手腕的几厘米远处,在那只被冷光灯打得纯白的手背上,似乎还能看见雷蛇视线的温度。过了一会儿,依旧望着地面的她把什么都没触碰到的手收回身边,和另外一只手掌一起覆盖在自己脸上。
室内充斥着雷蛇衣物的摩擦声,微弱,几乎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将房间拖入寂静中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雷蛇把脸从手掌上抬起来看向自己。没有悲伤,只是眼睛似乎睁大了一些,使得浅白的眉毛向上凸起了,“芙兰卡,”雷蛇的声音有些不平稳。颤抖。但空白的面容没有变化,但就像是眉毛抓紧了她的眼眸,而她的眼眸抓紧了某种感情,似乎一瞬间的松懈就会造成一种面容的崩塌,“啊……嗯。”
搭档没有再说下去,垂下视线,抿住了嘴唇,转头再次望向地板,又过了一会儿,牙齿扣紧了她的下唇,咬合处周围的肌肤向着牙齿尖端皱缩起来。
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向着医师点了点头。
出发那天和自己整理完行李后,优等生一声不吭地在宿舍抱紧了自己。芙兰卡一边轻轻抚摸雷蛇的背部,一边看向墙壁——每次这么做,自己都觉得穿过雷蛇蓝色尖尖的角,被划分出一个梯形形状的墙壁十分滑稽,有一次忍不住为这种荒诞的原因笑出声时,比自己矮小半个头的优等生似乎认为这又是在捉弄她,在自己怀里嘀嘀咕咕的样子也很可爱。
再过一个小时,在大家面前送自己上车的优等生会说些什么呢。
虽然准备旅行(她更愿意这么称呼)的这几天一直到现在心情都很差,但对雷蛇这样的期待感,却一直伴随在自己的想法身边,自从和她相互熟悉对方了之后,自己未来的期待里,总是有着雷蛇这个方方正正的家伙等着自己来拆封出早已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呀。
还有那些家伙,怎么说呢,即使带着期待感与免疫力,但别离之际,自己还是被山呼海啸般的俗套桥段将内心所充盈了。比如杰西卡被香草死死盯防的不敢哭出来的脸,憋的非常有趣,但碍于身份,都让自己没办法用这点打趣也有些遗憾;阿米娅难以抑制自身感情又不得不说的那一小部分用于送别的官腔套话,语气上的起伏,听起来也很有意思,等等等等。嗯……总之来了很多的意料之中的人,发生了所有意料之中的事,但这么多意料之中的东西展现在意料之中的时间里,芙兰卡自己却意料之外的感到了一种柔韧的安心感。
自然的,大家也开始揶揄雷蛇,把原本站在人群第二排还是第三排的她推到了最前面。
大家对那时候的雷蛇说了很多话,自己大多记不得了,但无论是多少次回忆起她,自己居然都能感受到那一天内心的某种聚焦感。
自己一直注意着搭档,所以芙兰卡能明白,无论是沉默的站在人群后,还是被推搡到自己身前,雷蛇沉默的眼神都一直追随着自己的身影。
人群安静了下来,察觉到大家的关注,她的视线终于稍微撇向了一边。
“离得远又有什么……反正我想要来看你,能空出工作时间,坐车也可以马上见到。”
吞吞吐吐的。
自己一时半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情,至少雷蛇平时是不会说出这么主动的话的,更别说有其他人在场,但知道这一点,自己也还是弄不懂内心产生了什么。
稍微有些糟糕的是,其他人也陷入了这份沉默。
这时,雷蛇走近芙兰卡,伸出右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照顾好自己,”
沉默。大段的。
“到时候我去接你回来。”
芙兰卡听到了动车进站前,铁轨上随着震动传来的,锐利而朦胧的摩擦声。
再过一会儿,列车便从隧道里冒出头来。
从喉咙到胸腔,又开始了伴随着刺痛的颤动。
现在遇到这种症状,咳嗽的剧烈程度她已经能忍住,但考虑到雷蛇马上就要与自己见面,总之还是咳出来比较好。
一阵秋风吹来,捂在嘴前的白色餐巾纸边缘开始随风飘摇,轻轻地剐蹭着芙兰卡的鼻沿,在咳嗽导致身体轻微震荡的晕眩感里,列车以一种混沌中参差不齐的快速感驶入了车站。
雷蛇会盯着窗外寻找我吧,这时她没有顾虑地想到了这一点,把咳出来的东西用纸巾包好,再用边缘稍微抹了抹嘴,转头张望,有一个垃圾桶正好在不远处。
对应的车厢出口出现了对应的雷蛇。
排在二三四五六、六个人身后的她,头上的两枚蓝尖尖已经套上了防护套,原本尖尖的位置,现在被两个毛绒绒的圆球取代,同时也看到了芙兰卡的她,向着搭档的方向高高举起了左手,芙兰卡看到雷蛇微微颤抖着的倾斜的肩膀,想象着雷蛇在人群中踮起脚尖时忽高忽低的脚跟,微笑着举起右手向着对方的方向摆了摆。
“芙兰卡!”雷蛇冲自己大喊到。
自己很没出息地,鼻子发酸了。
面前最后一个人终于走下了动车,雷蛇背着包,提着一小只行李箱,向自己这边快步走来,两人还差几米的距离时,雷蛇把行李箱立在身边,向自己小跑过来。
芙兰卡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向着雷蛇伸出了双手,在远处的雷蛇接近自己的过程中,自己就像是在捧着雷蛇她逐渐变大的身体。她想,是吗,自己从来没见过雷蛇这样热切地拥抱。
身体被轻微地撞击了一下,她忍不住轻咳出两声,在咳嗽所导致的呼气后,自己慢慢吸入雷蛇周身的空气,雷蛇抱住自己时,一只手不知道怎么地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之后又慢慢滑到自己的腰间,在感受着雷蛇缓慢地变化姿势时,自己也在享用着搭档身上久违的气息,最明显的当然是洗发水的香气,之后通过呼吸缓缓渗入自己体内的,还有雷蛇身上难以描述的身体的味道,说是汗味,但没有那种过激的炙热感,那是一种伴随着及其细微的盐味,以及肉体上难以描述的独立的味道,像是在树林嗅闻树木时,每一棵树都存在,但却无法统合的伫立感,但比起树木来,又多了温存的柔软……应该说这就是雷蛇身上属于自己嗅觉器官中的气味吧。
芙兰卡睁开不知道什么时候闭合的双眼,锁骨上雷蛇脑袋的重量感十分清晰,数次雷蛇的吐息而逐渐叠加起的余温在自己的脖颈处渐渐开拓起一小块她的区域。
这时候向前看去,即使雷蛇脑袋上套了那两枚防护套,面前依旧能看到被她的角分隔出的梯形形状,“是这样吗?”芙兰卡稍微低垂了视野,看向雷蛇灰白色的头发,“优等生?”
发现雷蛇的手想慢慢松开,她便使力又抱紧了雷蛇一些,雷蛇有些匆忙的也再次回抱住了自己(对雷蛇的这种小心思得忍住不能笑),然后她稍微抬了抬头。
这样角度就差不多了。芙兰卡垂下脑袋,将嘴唇贴在了雷蛇的头顶,银白色的头发上。
我的脑袋就像引信被点燃了一样,顿时觉得双颊变得滚烫起来,刚刚抬起的头马上又垂了下去,结果脸颊上芙兰卡她锁骨的凸起更加清晰了,我把放在她腰上的双手抬起来,试图握住芙兰卡的肩膀把她支开,结果再次被她一把抱紧,然后,像是在用我的头发磨她的嘴皮子似的,狐狸脑袋一下子埋在我的头发上蹭来蹭去,在头顶一片沙沙作响的眩晕之中,隐约还能听见芙兰卡她笑嘻嘻的哼哧声,完全就像是小孩子在胡闹。
“你这…..死芙兰……卡……也不怕被我的角…….头发被绞进…..去了啊!疼!”
完全和我在火车上预想的那么多种情况不一样,我还以为能再…..我不是那种扭捏的人,但我还以为隔了快大半年,和芙兰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能矜持一段时间。
然而现在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满脸通红的整理着自己脑袋上的头发,整理的时候不知道这只狐狸怎么弄的,好像真的缠住了几根,手指顺下去还有点痛感……和一点湿漉漉的,我反正不愿意去想是什么液体的东西。
结果抬起头,面前空空如也。
“芙兰卡!”我以为她又在捉弄我。
“啦啦,不要把行李箱忘记了哦。”
我回头望去,她正一脸开心的拿着我的行李箱走过来。
“能不能正经一点。”我想着如果真的有狐狸口水黏在头发上,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吧。
但看见芙兰卡轻快地拿着我的行李,我又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正经一点啊!”我呆板地重复着。
“可是,”芙兰卡见我伸手靠近行李箱,又把它拉回到自己的身边,“不是你自己想要抱我的吗?”
“什,什么啊,谁告诉你的!”
“喏,呈堂证供。”芙兰卡把我的行李箱立起来,拍了拍它的脑袋。
“哈?什么啊。”
“你不是自己急匆匆地把它抛下了吗?”
……..
“现在人证物证具在啦。”
“什么人证……”
我不自然地挪开视线,身后重新传来滚轮的声音,接着,一根手指伸过来,戳了戳我的脸。
“表情很不自然啊,优等生。”
芙兰卡提起我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走在我的身边。
“我来提吧。”这恐怕是最后岔开话题的机会了。
但虽说是打岔,我却怀着一种微妙的心情在等待着被芙兰卡捉弄。只是等了很久,或许不久,只是没有芙兰卡她的声音,车站的周围显得安静极了,只有我的行李箱不停滚动的声音让我有些安心地感到芙兰卡的存在。
转过头,还是能安稳地看见搭档她的全部,芙兰卡也微笑着看着我,只是突然安静的氛围,使得她的微笑更加牵引着注意。
我刚想先开口,搭档她便像是抓住了我的破绽一样出声了(像她作战时那样)。
“好久没看到你了,不想累着你~”
那是平稳而高兴的、久违的声音,比起语言上存在的可能性,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种单纯的、对于我存在的补足。
但笨拙的我依旧只能像刚刚那样,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是不是我总是倾向于遵循一种基于规则和经验的变通呢,使得我的某种敏感,并不能很好的由细微的动作所体现。
结果这句话之后,我和芙兰卡沉默地走了一段时间,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和她之间依旧保持着一种两人愉快的氛围,这应该都归功于芙兰卡吧。
出站这段时间,我和她随意聊了一些很浅的事情,甚至都没主动说起各自最近遇到的事,走下电梯之后,芙兰卡说她住的地方离车站比较近,我可能有些木讷,又建议她让我来拿行李箱,结果这次她捏了捏我的脸。
“坐了多久的车?”她问。
我想了想,换乘了两次,中途为了赶时间坐了一趟班车,这样是五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
“先是……然后……因为要赶上……”我后知后觉地才发现说完这一串干巴巴的话要不少时间,小心地看了芙兰卡一眼,发现她还是一副兴奋的样子,而且是她敏锐的个性吗,我看向左边的时候,发现她也正好在看着我,看了一会儿,把肩膀靠了过来,手背上的掌指关节刮蹭着我的手腕,我把头扭向一边,继续说起路程,
“如果赶不上,就要等到明天去坐到……最后,就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到今天八点四十到新田的这班。”
走在我身边的芙兰卡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出一个个地名和列车号,一直等到我说完。
“坐了快两天了,为什么不中途找个地方休息。”芙兰卡说。
她又蹭了蹭我的手背。
“因为想快点……快点到这里(见到你)。”
指节再次打在了我的手掌侧面,稍微有点疼,看向狐狸那里,她也像有第三只眼睛一样,再次同时看了过来,狡黠的笑容上,橙黄色的眼眸随着眼睑的开合,闪烁着焦急地忧虑。
当然,这种焦急也是狡黠的一部分,或者说焦急和忧虑都是基于一种婉转而开朗的狡猾所建立的。
我稍微扫视了一下周围,人来人往的。
在芙兰卡的手再次轻轻摇晃过来时,我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她。
……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牵手不能直接说吗。
“真绅士呀——”芙兰卡满面春光地凑到我耳旁,轻轻哼了一句。
我的脸色应该更红了。那种焦急感也是陷阱啊!就像她在作战时候那样,喜欢故意露出破绽,然后利用敌人的急躁切入。然而,并不是说我看穿了搭档的眼神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没看穿是对我的一种捉弄(当初就是我主动问了芙兰卡为什么要碰我的手,然后被她那么直白的要求弄得满脸通红),但看穿了依旧是另一种捉弄罢了,虽然如果芙兰卡直说的话,我也会牵手,但这样一声不吭的主动握住,我依旧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都是狐狸砧板上的肉……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毕竟我也很想更多地触碰她。
狐狸又把我握住的手松开了,但在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要被捉弄之前,芙兰卡马上重新触碰到了我的指尖,我看向她,发现她悠然自得地保持着步调看向前方,然后一个个的,将我的手指夹在她的指缝之中。
我和久违的搭档,十指相扣的漫步于路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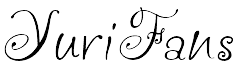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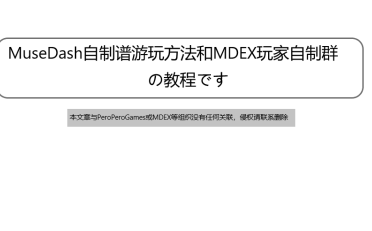


![[下载/搬运/纪录片/熟肉]Homotherapy(以爱之名:同志矫正治疗)[1080P][已完结][内嵌][2.73G][2019]](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2/fill_w372_h231_g0_mark_p2632286342.jpg)


![[下载/搬运/文学研究/汉译][桑梓蘭]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 [王晴鋒译] [臺大出版中心][已完结][2014]](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1/fill_w372_h231_g0_mark_1939a99778c51976e_1_post.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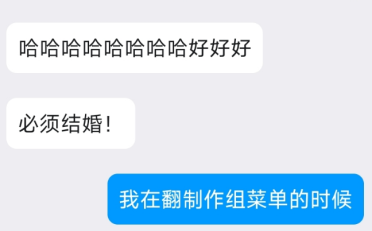
![[安利/音声/熟肉]ユビノタクト TS百合系列 资源汇总/剧情时间线整理2.0](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8/fill_w372_h231_g0_mark_24783d664e02bd3ad_1_post.jpg)
![[安利/游戏] 百合文字冒险《岩倉アリア》 [2024]](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6/fill_w372_h231_g0_mark_9731e61511876800_1_post.jpg)
![[安利/安价/熟肉]组曲&哈士奇考古笔记[未完结][2008]](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3/fill_w372_h231_g0_mark_455d38d4bfa7166_1_post.jpg)
![[在线/原创/小说]三无娘[堇色年华][中篇]](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1/fill_w372_h231_g0_mark_1405e3bee5d1661_1_post.jpg)
![[在线/同人/绘画]砂糖x盐[MaidCode幺零二三][happy sugar life同人]](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10/fill_w372_h231_g0_mark_453aa0770dc6cd30_1_post.png)
![[在线/同人/绘画]糖盐[MaidCode幺零二三][happy sugar life同人]](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9/fill_w372_h231_g0_mark_453676fd5369926e_1_post.png)
![[在线/同人/绘画]砂糖x盐[MaidCode幺零二三][happy sugar life同人]](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8/fill_w372_h231_g0_mark_4534c6c64be55e37_1_post.png)
![[在线/同人/绘画] 仙宫13 [MaidCode1023][一周一次买下同班同学的那些事同人]](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5/fill_w372_h231_g0_mark_45391535d266c8c2_1_post.png)
![[在线/首发/漫画/熟肉][深海 紺]恋より青く(比恋爱更青涩)[提灯喵汉化组][コミックオギャー!!][连载至18话][2022]](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9/fill_w372_h231_g0_mark_01-7.jpg)
![[在线/首发/漫画/熟肉][玉崎たま]無力聖女と無能王女~魔力ゼロで召喚された聖女の異世界救国記~(无用圣女与无能王女~被召唤至异世界的零魔力圣女救国纪)[提灯喵汉化组][コミック百合姫][连载中][更新至第6话][2024]](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5/fill_w372_h231_g0_mark_72.jpg)
![[在线/首发/漫画/熟肉][ひあるろん&達磨]小春と湊(小春和凑)[提灯喵汉化组][コミック百合姫][连载至21][2022]](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11/fill_w372_h231_g0_mark_468.jpg)
![[在线/首发/漫画/熟肉][森]姉になりたい義姉VS百合になりたい義妹(绝对想当姐姐的义姐VS绝对想搞百合的义妹)[提灯喵汉化组][マグシブ][连载至50话][2022]](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10/fill_w372_h231_g0_mark_13-49.jpg)
![[在线/翻译/首发/小说/熟肉][原作:動画投稿少女 作者:日日綴郎]【发布者自译】【真夜中パンち】深夜重拳[2024] 完结(不知道还会不会出)](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8/fill_w372_h231_g0_mark_QQ截图20240815103846.png)
![[在线/首发/小说/熟肉]ALTDEUS: Beyond Chronos Decoding the Erudite(阿尔特斯:超越时空 解读朱莉)[个人翻译][短篇小说][已完结][2021]](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8/fill_w372_h231_g0_mark_973161b1b510a60c_1_post.jpg)
![[在线/首发/小说/熟肉]まな板のうえの恋(砧板上的爱/Love upon the Chopping Board)[发布者自译][6/15][1993]](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2/fill_w372_h231_g0_mark_13537ac46652cba3ed_1_post.jpg)
![[在线+下载/搬运/动画/生肉+熟肉]海のまにまに(任由海波荡漾)[Aki惊蛰][4K][1080P][已完结][YouTube][Bilibili][MV][YOASOBI][2023]](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2023/03/999.gif)
![[在线/转载/纸动画][推特]爱的日子[21MB][2022]](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5/fill_w372_h231_g0_mark_MGT@0U4YYIRU6TA@QSN.png)
![[在线+下载/首发/音声/熟肉]【魔法少女にあこがれて】【ASMR】マジアベーゼにいたずらされて【耳ふー・咀嚼音・耳かき】(【憧憬成为魔法少女】【ASMR】魔法枫糖的恶作剧时间【吹耳 · 咀嚼音 · 掏耳】)[YouTube][百合音声同好会][2024]](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4/01/【魔法少女にあこがれて】【fill_w372_h231_g0_mark_ASMR】マジアベーゼにいたずらされて【耳ふー・咀嚼音・耳かき】-KADOKAWAanime-1.jpg)
![[在线/首发/音声/熟肉][RJ307502]どうしていつもこうなるのっ!?(为什么总是会变成这样啊!)[百合音声同好会][2020]](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9/fill_w372_h231_g0_mark_37NG6581JV1_7UQ9P.png)
![[下载/首发/音声/熟肉][YouTube]不会死去的她与忧伤的雨天[百合音声同好会][2021]](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8/fill_w372_h231_g0_mark_PMH8X4FYWW_IW2K8NM92.png)
![[下载/首发/音声/熟肉][RJ246088]ランドリー(White Laundry Magnolia)[百合音声同好会][2019]](https://yuri.website/wp-content/uploads/thumb/2022/08/「ランドリー」イメージイラストfill_w372_h231_g0_mark_.jpg)











非常好文章,爱来自黑钢👍
好看爱看太尊了[室2]